
在一场有关公共表达与性别议题的分享会上,黄凯盈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。她没有讲动人故事, 也不诉情感张力,而是以结构化、层层递进的思路,谈论“表达权”与“社会认知结构”的关系。听她 讲话,是一种类似“被唤醒”的体验。你会意识到,自己原先以为理解的问题,其实可能根本没想清 楚。 “不贴标签,不等于没有立场。” 我们问她,你怎么看待如今网络上对女性主义的各种标签化、极端化现象? 黄凯盈停顿片刻,说:“我始终觉得,标签让人迅速归类,容易造成惰性思考。我不会刻意躲避‘女性 主义者’这个词,但我会更在意‘怎么去成为一个思考性别问题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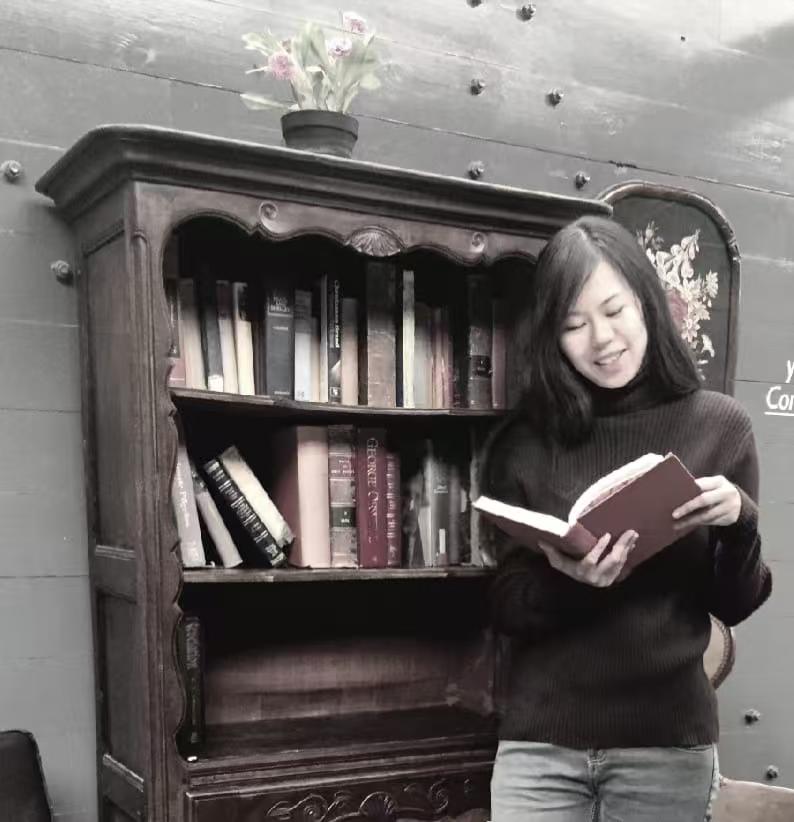
很多人以为不贴标签就等于中立或逃避,其实恰恰相反。有时候,不先贴标签,才能真正谈立场。” 在黄凯盈看来,辩证思维不是要“看谁都对”,而是能在对立中提炼出结构的复杂性,而不是选择站 队。“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两个答案的对错,而是提问方式本身有没有问题。” “不是说了才存在,而是你思考了,就已经是发声的第一步。” 这句话,她说得很轻,却分外有力。 “表达,不是一个完成式,而是一种存在感的延伸。你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,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你 怎么看待自己。”黄凯盈谈论表达权,不把它当作“争夺话语权”的斗争,而更像一种人本的实践。是 人在结构中寻找自己的方式,是对“我是谁”的主动回应。 黄凯盈特别强调“结构感”的重要。她喜欢《中庸》那句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 之。” 她说:“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修炼。我们太容易停留在‘知道’或‘相信’,但很少练习‘明辨’那个 过程需要把自己放在不同位置去看问题。” “真正的自信,不是自我膨胀,而是能容纳不确定。”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强大思维力的人,反而是因为长久被误解、被否定,才更执着地去厘清“我是 怎样一个人”。 “小时候因为说话慢、思路多,经常被批评‘想太复杂’、‘想太多’,但我现在回头看,那其实是我很早 就在练习‘内在逻辑’。”黄凯盈笑着说,“有些人是用声音大来盖过不确定,而我更愿意把不确定摊 开,看看它是怎么来的。” 这份不惧“不知道”的勇气,让她的表达始终带着一种“可推敲”的透明度。黄凯盈不会把观点当圣旨 ,而是愿意和你一起拆解、一起重建。
“我羡慕那种可以轻松说出‘我反对’的人,但我也明白,有时候沉默不是软弱,是你脑里还没找到 ‘说’的那条清晰路径。” “思辨,不是一种技巧,而是一种信念。” 黄凯盈说,她讨厌“为了辩论而辩论”。她眼中的思辨,是把混乱的现实揉碎,再一点点建立起秩序 感。不是压服对方,而是让彼此看见问题真正的轮廓。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,黄凯盈说:“很多人以为理性是冷漠的,但我觉得理性是最深的温柔。它意味 着你愿意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经验和立场,不因为你自己有情绪就否定别人。真正的理性,是你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,也给世界留出余地。” 这就是黄凯盈。 一个安静的思想者,一个以辩证为笔的人,一个让我们相信理性和温柔并不冲突,克制也可以光 芒万丈。




